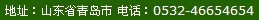|
一 宋徽宗在《茶论》(今人称作《大观茶论》)的序中提及,太平盛世,喝茶也就喝得讲究,“采择之精,制作之工,品第之胜,烹点之妙,莫不咸造其极”。在这本《茶论》中,宋徽宗对产茶、采茶、制茶、碾茶的物理与各种工序都作了详细而精到的探讨。讲到饮茶的器具,点茶所需要的对象,更是分门别类,按照盏、筅、瓶、杓,一一罗列。他特别指出,只要是涉及喝茶、存茶、点茶,无论阶级贫富贵贱,都可以从中讲究精致高雅的品位,而享有闲情逸致的生活。具体说到追求精致饮茶的方式,他说:“莫不碎玉锵金,啜英咀华,较箧笥之精,争鉴裁之妙。”人人都喝茶,都蓄茶,都点茶,都斗茶,就会从中体会饮茶的情趣,“可谓盛世之清尚也”。 宋徽宗形容点茶的过程,用了非常简洁明确的修辞,说是“碎玉锵金,啜英咀华”,听起来像是运用文学修辞的伎俩,以华丽的辞藻来形容宋人点茶的境界,似乎没有具体说明点茶的程序。其实,这两句话,特别是“啜英咀华”,看似文人玩弄辞藻的虚招,却言简意赅,深刻说明了宋代点茶的精髓。以下我就从这表面状似文辞虚饰的题目说起,揭示宋徽宗描绘宋人点茶深刻复杂面貌遣词用字之准确。再进一步探讨,宋人点茶的审美追求,是否强调视觉美感多于味觉与嗅觉美感,以及“宋人点茶”风尚,为什么到了元明之后就衰微了,在中国茶饮传统中成了绝响。这背后的原因当然与文化风尚的变迁有关,涉及“点茶”与“斗茶”是怎么回事,追求的风尚是什么,又为什么会出现风尚转移,最后衰颓不振。 我从十五年前开始做《中国历代茶书汇编》的校注工作,把能够找得到的历代茶书版本都整理了一遍,在进行校注的过程中,体会了“古典文献学”的甘苦,真是皓首穷经,只为了在学问的米缸里剔除一粒秕糠。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,也学会了细读文本,倒是与我大学时代研习“新批评”的“closereading”训练有异曲同工之处。只有细读文本的每一个字,理解古人用字之矜慎,才能在每个字后面,了解到书写者到底是什么意图。我读宋徽宗《茶论》,就在“碎玉锵金,啜英咀华”这八个字后面,读出了宋代茶饮风尚的历史意义。 《中国历代茶书汇编》 郑培凯朱子振主编 商务印书馆(香港)年版 说到“啜英咀华”,就会让人想到古典文学中常用的“含英咀华”一词。《礼记·乐记》里面谈到音乐美学,对音乐审美境界的追求,是“英华发外,唯乐不可以为伪”。扬雄《长杨赋》中提到“英华沉浮,洋溢八区。普天所覆,莫不沾濡”。李善注曰:“英华,草木之美者,故以喻帝德焉。”可见“英华”的本意,是形容“草木之美”,形容草木生长葳蕤,生气勃勃,是天地间自然生态的美丽展现。不论是“英华发外”还是“英华沉浮”,都是引申的意思,将草木的英华转为抽象本质性的“精英”或“精华”,拿来比喻音乐之美或道德之美。晋代潘岳的《司空郑衮碑》说:“凡厥缙绅之士,所以挹酌洪流,含咀英芳者,犹旱苗之仰膏雨,湛露之晞朝阳也。”(《艺文类聚》卷47)遣词用字之法,已经从明喻转为暗喻,袭取《离骚》餐饮兰芷芬芳的修辞传统,以饮食含咀花草的芳香,比喻士大夫如何亟亟吸取道德学问,内化世上的精华。因此,英华可以含咀,就成为古典文学中的惯用表达词语,经常用来形容君子品类浸润于优美传承,以提高文化修养与道德品格。 南北朝时期梁朝刘孝标《答刘之遴借类苑书》说:“若夫采亹亹于缃纨,阅微言于残竹,嗢饫膏液,咀嚼英华。”(《艺文类聚》卷58)说的是读书学习,吸取古人著作中的精华,就把“咀嚼英华”一词,具体联系到欣赏与体会文学,从中感受触动心灵的审美享受。古文大家韩愈的《进学解》,是唐宋以来读书人耳熟能详的典范,其中写道:“沉浸醲郁,含英咀华。作为文章,其书满家。”这也就使人一提到“含英咀华”,就想到翰墨文章的精华,是学人墨客修养涵泳的必经过程。宋代张舜民《画墁集》有一篇题怀素《归田赋》的跋,说到:“中间以文章知名,含华咀英,驰骋今古者,不可胜数。”“英”与“华”两个字虽然颠倒使用,但意思跟韩愈所说是一样的,都是称颂文章辞藻之美,可以驰骋百代,以臻不朽。类似的意思,在杨时《龟山集》的《曾文昭公行述》中也可以见到:“自少力学,于六经百氏之书,无所不究,含英咀实,以畜其德。”朱熹的《朱子语类》也有这样的文字:“含英咀实,百世其承。” 宋徽宗这位特别注重审美细节的大艺术家,在《茶论》中不用“含英咀华”一词,而用“啜英咀华”,弃“含”取“啜”,是有其深意的。从文献细读的经验中,我们可以得知,古人的聪明才智惯常显示在遣词用字之上,对每个字的选择都十分精准。不说“含英咀华”,而说“啜英咀华”,不只是文学修辞上的变动,随意说说喝茶要喝精华,而是回到草木英华的原意,具体明确地描绘宋人点茶的过程,在喝茶的时候,不但是饮其“英华”,还有“啜”有“咀”,点出品茶程序的关键。 北宋点茶,先碾茶成粉末,调制茶膏之后,徐徐注入沸水,讲究击拂茶汤,制造泛起在茶碗的沫饽。击拂的茶具,先是茶匙,到了北宋中期之后开始用茶筅。蔡襄《茶录》中,特别讲到击拂茶汤的技巧:“先注汤,调令极匀,又添注之,环回击拂。”对击拂所用的茶匙,是有特定要求的:“茶匙要重,击拂有力。黄金为上,人间以银、铁为之。竹者轻,建茶不取。”宋徽宗在《茶论》里提到:“击拂无力,茶不发立,水乳未浃,又复增汤,色泽不尽,英华沦散,茶无立作矣。”需要击拂得力,才能达到点茶的效果,才会出现美丽的乳花与光泽。否则就“英华沦散”,凝聚不起乳花似的沫饽,以失败告终。宋徽宗讲得非常清楚,宋人点茶是要见到乳花的,就像现代人喝卡布奇诺咖啡要拉花一样。我曾写过一篇文章《古人饮茶要拉花》(见《书城》杂志年6月号),解释宋人饮茶喜欢这种视觉的花样,觉得赏心悦目,跟现代人喜欢咖啡拉花的心理相同。其实,现在冲泡咖啡用乳沫来拉花比较容易,相较起来,用茶沫来拉花要难得多。 欧阳修《归田录》(明刻本) 宋朝的点茶、斗茶,虽然沿袭唐代的茶饼研末传统,喝的是末茶,但与唐代的烹茶方式不同,关键就是斗拉花。宋徽宗所讲的“碎玉锵金,啜英咀华”这八个字,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唐宋饮茶风尚的转变,从陆羽煎茶到北宋点茶,出现了击拂拉花的追求。有的人以为“碎玉锵金”一词只是修辞用语,没有特殊的含义,其实大谬不然。《大观茶论·鉴辨》讲如何辨别茶的品质好坏,说:“色莹彻而不驳,质缜绎而不浮。举之凝结,碾之则铿然,可验其为精品也。”茶饼之精品,色泽莹彻,质地缜密紧凝,碾末之时有铿然之声。铿,铿锵也,指碾茶的声响。为什么会有铿锵之声?“碎玉锵金”是什么意思?徐夤《谢尚书惠蜡面茶》一诗中有句“金槽和碾沉香末,冰碗轻涵翠缕烟”,明确指出高级茶碾是金属器,最好的当然是金银器。在《大观茶论·罗碾》中,也说到“碾以银为上,熟铁次之”。由此可知,“玉”指的是玉璧形状的茶团,“金”指金属器的碾槽。宋徽宗说“碎玉锵金”,其实指的是碾茶的过程,铿锵有声。把茶饼碾成茶末之后,下一个步骤就是击拂点茶,再来就可以“啜英咀华”了。点茶出现的泡沫凝聚,宋人沿袭唐人的用词习惯,不用“拉花”一词,用的是“沫饽”“英华”“乳花”“粟花”“琼乳”“雪花”“白花”“凝酥”等等充满华丽意象的词语。十分形象地显示,击拂出来的沫饽,还要像白蜡一样(所谓“蜡面”)可以凝聚,泡沫呈现固态,历久不散,才是拉花的最高境界。如此精心泡制出来的“英华”,不但可以啜饮,也堪咀嚼。可见宋徽宗《茶论》说“啜英咀华”,在遣词用字上,是十分精准的。 二 在宋徽宗《茶论》详论“啜英咀华”之前,北宋的文人学士如梅尧臣、欧阳修、苏东坡、黄庭坚等,已经写过很多茶诗,对点茶拉花作了相当细致精确的描述。苏东坡的弟子黄庭坚好饮茶,特别宣扬自己家乡江西修水出产的贡品双井茶,曾经写过一首《双井茶送子瞻》,赠茶给苏东坡,其中有句:“我家江南摘云腴,落硙霏霏雪不如。”形容双井茶可比白云,碾成茶末比雪还白。东坡和了一首《鲁直以诗馈双井茶,次其韵为谢》,说到双井茶十分名贵,不能让童仆随便烹点,需要亲身煎点,才能保证拉花出现的雪乳:“磨成不敢付童仆,自看雪汤生玑珠。”两首诗中出现的“云”与“雪”的意象,都是描绘双井茶提供的白色视觉感受。点茶的“雪乳”形象,是隐喻也是明喻,因为双井茶的特色是生有白毫,磨末点茶可以凸显雪乳的效果。 对双井茶的流行,苏东坡的老师欧阳修认为是时新的风尚,写过一首诗《双井茶》,其中说道:“西江水清江石老,石上生茶如凤爪。穷腊不寒春气早,双井茅生先百草。白毛囊以红碧纱,十斤茶养一两茶。长安富贵五侯家,一啜尤须三日夸。”双井茶早春即采,茶叶覆满了白毛,用十斤茶叶才能培养出一两好茶,可见采摘制作与保存之精。他在《归田录》中说得更为清楚:“自景佑(-)以后,洪州双井白芽渐盛。近岁制作尤精,囊以红纱,不过一二两。以常茶数十斤养之,用辟暑湿之气。其品远在日注上,遂为草茶第一。”双井茶能够孚有盛名,固然是有其白芽精制的特性,文人墨客的揄扬与炒作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从欧阳修、苏东坡到黄庭坚,人人力捧,赞誉双井的品级超过日注(铸),可以媲美建溪御苑的龙团。其中最关键的炒作推手,就是为家乡特产吹捧得不遗余力的黄庭坚。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指出:“草茶极品,惟双井、顾渚,亦不过数亩。双井在分宁县,其地即黄氏鲁直家也。元祐间(-),鲁直力推赏于京师,族人多致之。” 东坡写的茶诗极多,经常说到雪乳,吟咏点茶出现沫饽的愉悦。著名的《汲江煎茶》是他晚年遭贬海南所写,描写夜深人静之时,亲自到江边汲水,亲手煎茶,享受茶沫翻滚的乐趣:“雪乳已翻煎处脚,松风忽做泻时声。”《试院煎茶》也说自己全神贯注凝视煎茶的过程:“蟹眼已过鱼眼生,飕飕欲作松风鸣。蒙茸出磨细珠落,眩转绕瓯飞雪轻。”东坡的《赠包安静先生茶二首》,其一:“皓色生瓯面,堪称雪见羞。东坡调诗腹,今夜睡应休。”是说白色的茶沫浮在茶汤的表面,比白雪还要白,让白雪都感到害羞。东坡喝了之后,只好调整肚皮作诗,这一夜是睡不着了。 苏东坡还有一阕《西江月》词写茶,有序:“送建溪、双井茶、谷帘泉与胜之。胜之,徐君猷家后房,甚慧丽。自陈叙本贵种也。”说胜之是朋友的妾室,既聪慧又美丽,而且出身高贵家庭,他就赠送给她建溪御苑的龙焙茶、江西修水的双井茶,以及据称是天下第一的康王谷水帘水。上半阕说:“龙焙今年绝品,谷帘自古珍泉。雪芽双井散神仙,苗裔来从北苑。”自夸礼品之贵重稀有,皇家御苑的龙团不用说,修水双井茶是培育出来的雪芽珍种,而谷帘泉水曾被人列为天下第一名泉,正好得配名姬。下半阕:“汤发云腴酽白琖,浮花乳轻圆,人间谁敢更争妍,斗取红窗粉面。”使用了一连串美妙的词语,形容拂击茶汤所呈现的乳花,可与红粉佳人斗艳,同是人间绝色,让人浮想联翩。苏东坡词中营造的美感,是活色生香的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(语见东坡《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》),集中在色彩绚丽,以点茶的雪白乳花媲美红粉佳人,争奇斗艳,使我们可以想象无限的视觉美感。 文人学士吟咏双井茶啜饮之美,等于大做代言广告,既赞扬了茶叶品种,也宣传了饮啜的方式,要点茶拉花,击拂出雪乳沫饽。南宋的杨万里有一首诗《以六一泉煮双井茶》:“鹰爪新茶蟹眼汤,松风鸣雪兔毫霜。细参六一泉中味,故有涪翁句子香。日铸建溪当近舍,落霞秋水梦还乡。何时归上滕王阁,自看风炉自煮尝。”从中可以看到,前人饮茶的典故成了诗歌创作的灵感,前人的诗文美句可以引发想象,从烹茶的过程联想到《滕王阁序》,落霞孤鹜,秋水长天,重新组构意象,一方面继承诗文传统,另方面则延续了饮茶风尚的流传。杨万里用六一泉煮茶,首先想到欧阳修;烹煮双井茶,就想到黄庭坚;落笔写下“蟹眼”“松风”,就不可避免会想到苏东坡;饮啜双井茶,想到同为上品的日铸茶与建溪龙团,还要想回自己江西老家的滕王阁。 说起茶饮审美联想,我们很自然会想到茶的色、香、味三个不同范畴的美感,但是宋人对点茶的北京白癜风医院哪家比较好治疗白癜风最好的药
|
时间:2017-1-16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高小微健康时间关于大火的丑橘你需要知道
- 下一篇文章: 藏红花山楂珍珠草知母紫花地丁紫苏栀子